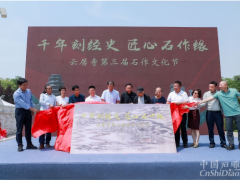石在远方
石雕,直白去讲便是石头的雕刻作品,在匠人的加持下,各种可雕、可刻的石头,被技艺、手法“锻造”出来具备空间可视、可触的艺术轮廓,如镜子一样折射出生活的边边角角,还有雕刻作者的审美感受、情感乃至理想。在人类还与大地没有分家的时候,石头的历史就开始萌芽了。时间深处,敬畏着自然的先民,用最古老也最笨拙的工具——石器,打磨着生活,且从未停止。而在包罗万象的艺术门类中,也再没有哪个类别可以超越石雕的古老。显然,这时代的人类文明万马齐喑,唯有石头的故事在风雨中低声吟唱。
若是用锄头刨拉历史,石雕的寿数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其中,石刻岩画乃是原始艺术家创作的主要形式。例如,阴山岩画对狩猎与动物的钟爱始终如一。
待原始先民告别了采集、狩猎经济,转入了新石器时代,便又出现了以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石磨盘、磨棒为代表的石雕作品。它用砂岩加工而成,外观则被“普及”为鞋底状的几何样式,看起来工整大方、重心稳定,但加工难度较大,需要在敲打、切割、修整中“渡劫”。此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古石雕技法的另一源头——线雕。而且此种线刻石雕的形式在后来历代的石雕创作中,被运用得最为广泛。
而到商周时期,文化特征、宗教强化以及艺术风格的迅速转变,使得这一时期的石雕艺术也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衍变。譬如,商代社会尊奉万物有灵,人们往往尊崇动物为神灵,受此影响,尚属粗放的石雕艺术家,便偏爱于对动物领域的实践,并进行了抽象化的探索。
岁月石歌
此后,在岁月漫长的打磨中,石雕艺术的创作水平不断地爬升。不同朝代,石雕在类型、样式和风格上都有很大变迁。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审美,始终在追赶和迎合着不同的社会环境。
待至大秦一统的到来,石头开始比皇朝更有所恃。秦代《三辅黄图》里明确记载,曾有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被刻于咸阳横桥,修始皇骊山陵时亦刻下一对高达一丈三尺许的石麒麟。遗憾的是,这当年真实卧躺过的石雕如今已只能由笔画勾勒,于简牍里存活。
此后到了汉王朝,石雕艺术愈发蓬勃。彼时的石雕艺术出现了园林装饰雕塑、丧葬明器、画像石、木石雕刻以及各类石雕工艺品。颇为著名的例证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对大型石刻,亦是我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即原先位于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常家庄,被冠以“汉昆明池石刻”之称的牵牛石像以及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它们均是由坚固的花岗岩雕刻成的高大的石像形体。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发展此时的石刻艺术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我国主要的大型石窟及其造像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精雕细琢的形象处理和装饰的合理构图,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发展。一方面,在当时的石窟外廊上,石工以极其精湛的技艺塑造了仿木结构的石窟建筑形式,为之后的石刻建筑奠定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典建筑样式以及装饰构件上的丰富多彩,也在石雕艺术中各自生长,有了不同方向的发展。
此外,石雕装饰纹样的愈加丰富也是这一时期宗教发展带来的变化。其中,飞天主题最是备受追捧。风姿各异、活灵活现的天使形象,最能反映出佛界的灵性。而鸟纹和繁花茂草装饰成的龛楣,几可比拟瑰丽的华冠。经过了佛像背光的火焰纹突出后,肃穆端坐的佛像更显神圣。
至了隋唐,大一统的到来像是给整个艺术界安上了“三脚架”,作为中华艺术瑰宝之一的石雕技艺持续稳定发展而形成新的高潮。
隋唐石刻艺术的伟大,皆因它多凭借庄严劲健的造型风格而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建筑和都市景观之中,成为装帧丰都大邑的依凭。而关于题材的选择,隋唐的石头雕塑已是愈见丰满,有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也有供玩赏的小型雕塑艺术品(如儿童玩具等),还有用于建筑或器皿装饰的工艺雕塑。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雕塑艺术的繁荣,文献中有关艺术家的记载也较过往多了起来。在唐高祖献陵的石犀上,便留下了“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的题名。
于隋唐时代的石雕建筑,是石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建筑艺术的范例,首推建成于隋大业年间的河北赵县安济桥(即赵州桥)。从安济桥的构件分析,隋唐时代的建筑在运用石雕构件上,要更为普遍,成就自然也更突出。此时,建筑与雕刻装饰的深入融合,无疑催化了隋唐石雕艺术的生长。
赵州桥上的精美石雕
石雕作品《飞天》
时间漫步,从盛唐踱步于明清。石头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大放异彩。众所周知,明清的宫苑、陵邑规模十分宏大,附丽其中的建筑石刻艺术也取得了不少创新发展上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故宫。
明代故宫前的白石华表为多种雕刻手法塑造的空前建筑装饰,乃至故宫主殿的台基、阶梯栏杆、走道、中庭、石桥,无不是种种石雕艺术形式的“强强重组”。另有明清两朝的皇宫园林——天坛,其主体建筑之下的基座、白石圆坛、石构件上尽皆饰满了石雕的华丽。再者,安徽凤阳的皇陵、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十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等处,都保留有大量的明清陵墓石刻。
石落中华
无疑,石头的故事是绵长的。而在它与中华文明“反复纠葛”中,成了被风吹散的花种,四散在万里锦绣中。尔后,在福建惠安、浙江青田、河北曲阳、山东嘉祥等地开出了最绚烂的花朵。
福建惠安雕艺的传承颇为久远,源于黄河流域的雕刻艺术同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的融合,最后形成了精雕细刻、纤巧灵动的南派艺术风格。从技艺上讲,惠安石雕主要青睐圆雕、浮雕、沉雕、影雕等几大类别。其中,沉雕主要用于建筑墙面的装饰及碑塔、牌坊、摩崖石刻、匾额、宅居楹联等,以线条造型为主要特色。譬如南京雨花台纪念馆的《日月同辉》等大型石雕便是典型的代表。如今,惠安县自己便拥有一座“中国雕艺城”,汇集上百家以石雕为主的雕艺企业入驻,气势鼎盛。
浙江青田石雕则以其秀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广受推崇,享有“石头上绣花”的美誉。它自成流派,以写实尚意为基调,细腻精巧,奔放大气,形神兼备,手法有圆雕、镂雕、浮雕及线刻,工序主要有相石、开坯、粗雕、细雕、封蜡、润色等。
福建惠安石雕
浙江青田石雕
历史上,河北曲阳石雕亦不逊色。从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阿房宫、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尽皆留下了曲阳人的凿刀痕迹。
自古而今,山东嘉祥当地便流传着“家家闻锤响,户户操钎忙”的俗偈。中国最早的石雕狮子——“武氏墓群石刻”便是出自嘉祥。在后来的发展中,它的突出作品以人像石刻为多。例如,屹立在安徽的焦裕禄、雷锋雕像,立于日本足利市泗水町的大型“孔子行教像”(世界孔子像之最),还有韩国的“释迦牟尼大佛”、济南泉城广场的雕塑长廊、泗水泉林“中国第一驮碑”等大量优秀作品。
河北曲阳石雕
嘉祥武氏墓群石雕
不论是惠安、青田、曲阳,又或者嘉祥,似乎都在证明着一个道理,在现代与传统的对决中,源自古老的石头在经过了时间的转身之后,终究未与文明背道而驰。
图文来源:中华民居